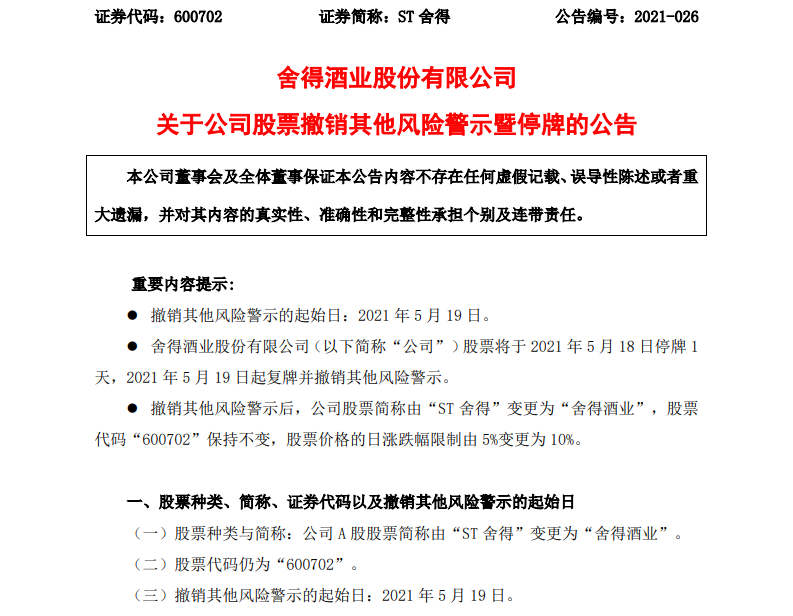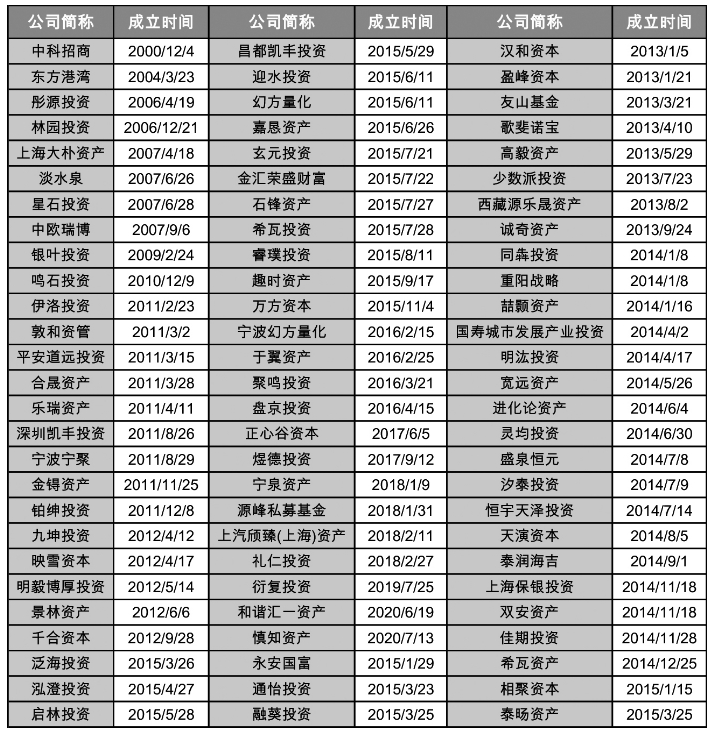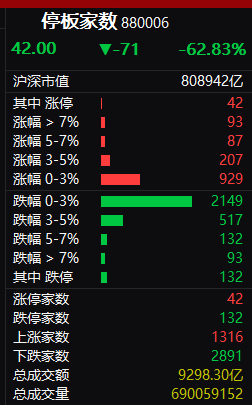从2020年到2021年,中文播客领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很多观察者感叹:中文播客元年来了。播客作为一个新蓝海,吸引越来越多创作者入场,也成为互联网巨头争夺的目标。
“去年疫情期间,大家都宅在家里,有很多空闲时间需要打发,于是很多人开始听播客,做播客。”去年7月,电台主持人方舟做了一档音乐播客节目《周末变奏》,两年前,他与京沪两地音乐从业者朋友开始了一档以分享歌单为主的播客《Music ONLY Podcast》。他对第一财经分析,中文播客之所以在2020年蓬勃兴起,疫情占了不小的因素。
据播客搜索引擎ListenNotes数据显示,去年4月,中国大陆播客数量达到10000个,到12月31日,播客数量增至16448个。打开喜马拉雅FM、蜻蜓FM、荔枝FM三大音频平台,播客入口都十分醒目,小S、黄磊、马家辉等明星名人都受邀在喜马拉雅做独家播客,以名人效应拉动流量。
中文播客另一个趋势是,许多媒体人开始入场,看理想、新世相、GQ等专业媒体、出版机构也纷纷上阵,成为这个赛道的优质内容生产者。一群驻美记者创立了《声东击西》,前文化记者程衍樑创立《忽左忽右》,三位女性媒体人傅适野、张之琪、冷建国则创立《随机波动》。纵观媒体人的播客,虽关注的话题各有不同,几乎都在口碑与流量上获得双赢。
互联网平台更围绕播客开启新一轮抢占赛。去年3月,即刻推出泛用型播客客户端“小宇宙”,迅速成为播客领域流量代表。之后,快手推出播客产品“皮艇”,百度播客客户端上线“随声”,荔枝推出有别于荔枝FM的“荔枝播客”,网易云音乐从“电台”改版而来的“播客”版块,都纷纷将播客视为新的流量增长点。今年3月,阿里也宣布进军播客市场。
中文播客的风靡,就像是传统广播的一次“文艺复兴”。人们开始讨论,播客是否能像2012年微信公众号初登场、2016年知识付费兴起那样,成为下一个风口,下一世代的媒体主流。
播客能不能商业化?变现是否有可能?只有解决这些疑问,才能决定中文播客是否能摆脱“小众”标签,以及能走多远。
播客,“小众”乌托邦之地
播客不算新鲜事物,早在2004年,英国媒体就以Podcast来定义互联网音频,所谓Podcast,是由“iPod”和“broadcast”两个词合并而成的全新词汇。
很长一段时间,播客都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发展。直到2014年,一档名叫《Serial》的播客节目诞生,主播以美剧般的节奏讲述一桩15年前的谋杀案,层层递进的悬疑引来无数听众追捧。
人们发现,播客也可以做得生动、有趣而充满个性。许多美国传统广播电台从业者开始进军播客,无论节目的制作质量与数量,都大幅增长。据2019年的数据统计,半数以上美国人听过播客,12岁以上的美国人每月平均有9000万人收听播客,这个数字占据全美人口的32%。
在中国,中文播客的发展更为缓慢。2013年,中文播客数量不到三位数,2017年之前,几乎没有人在全职做播客。随着网络听书、音频直播、知识付费等业务模式为主的网络音频模式不断酝酿,中文播客终于在疫情这一年迎来爆发期。
方舟既是传统广播行业从业者,也是播客主理人,能清楚感受到两者的区别。广播24小时不间断,更像是一种公共服务,陪伴人们日常生活,随开随听,节目内容调性平稳,强调持续而中性的信息量输出;而播客的订阅则是反公司化的,往往以话题为主导,听友对播客内容的兴趣、喜好和认可是收听的先决条件,也意味着播客内容的自由度、信息浓度都更高。
他认为,播客是通过RSS分发的方式来传播,是去中心化的。这使得播客更像是一个小众的乌托邦之地,每个人都可以像一位专栏作家一样,在这片自由领地做自己想谈论、想输出的内容。他从播客上体会到互联网时代早期的平民主义,入门门槛低,人人都可以做,无论是话题内容还是时长、频率都没有任何限制,“虽然播客是以语言为主要载体,但只要是声音呈现,无论对话、独白、聊天,都可以被纳入进来。”
“小宇宙”每日会有三条推荐内容,往往都围绕着艺术、人文历史、文化观察、两性性别、都市白领、内卷等社会议题。在喜马拉雅播客频道,则可以看到人文艺术、影视娱乐、生活方式、科技商财、体育和职业成长的细分栏目。无论是热门话题还是冷门内容,都能在播客上找到涉猎。
尽管中文播客时间不长,已形成了不同的风格。小众的播客圈如同一个小江湖,南北方播客被归纳为两派风格。以北京和天津为主的北方播客偏向“闲聊派”,《大内密谈》《日谈公园》等都以拉拉杂杂的聊天谈话形成强烈风格,突出主播个人风格,把聊天做成节目。而以上海为主的南方播客则偏向“网课派”,这类播客往往有准备,有知识点和话题讨论,听感更有节奏、更精致,信息传播的效率更高。
不同播主的自由化表达,不仅让播客内容百花齐放,更能让不同价值观的输出筛选出高黏性听众。
像《日谈公园》这样的播客,从一开始就决定以聊天的方式自由发挥,不需要过多准备,要的就是随意,聚集起气味相投的人群。而方舟的《周末变奏》,往往需要写详尽的文稿,在《乐队的夏天》热播时邀约热门乐队来对谈,也需要漫长的沟通期,时间成本极高,他认为,“现在做播客还没有一套约定俗成的体系,没有规范与模板,每一个播客节目的定位、构想、投入的精力都没有可比性。”
摸索中的商业化
在美国,播客早已实现商业化,成为发展最快的广告媒体,仅2020年播客广告收入就接近10亿美元。而中文播客的商业之路,仍十分漫长。
2013年上线的中文播客《大内密谈》直到2018年才摸索成一家为以盈利为目标的公司。另一个商业化道路走得最早、也是连续五年拿到苹果播客年度精选的中文播客《日谈公园》,获得头头是道基金的数百万天使投资,单期贴片广告报价最高达到30万。
程衍樑与朋友创立的JustPod,旗下有《忽左忽右》《杯弓舌瘾》《去现场》等16档原创播客节目,月度听众超过200万,仅今年上半年,JustPod的广告营收已达千万,不依靠投资,就能养活15位全职员工。
但现实是,除了头部的几家播客公司开始自负盈亏,主流播客都是不赚钱或是亏本的。
“许多人在焦虑商业化的问题,在蜜月期之后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。”资深产品经理刘飞是播客《三五环》的主理人,他做播客的目的,更多是想留下自己与朋友聊天的过程,把有价值的观察和思考分享出去。他认为,目前中文播客的商业化依然在缓慢探索中,大多数播客的商业化之路很可能是to B而非to C。
方舟发现,目前播客的商业化路径与微信公众号、直播带货和Vlog相比,并没有太多变化,就算主播在节目中做电商直播,带货效率也会很低,“我们瞥一眼文字就能获得很多信息,15秒短视频也比播客更有效。播客是线性的,是看不见摸不着的,只能听,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说,效率很低。它的用户黏性更多来自一种气味相投。”
尽管中文播客看起来热闹,但据他观察,很多播客主凭兴趣入门,节目做不过三期就放下了。除了头部几个播客可以全职,中腰部播客主都凭着一腔热忱“用爱发电”,用业余时间做播客。从长远来看,播客一旦缺乏盈利模式,仅凭兴趣也难以长期稳定地持续做下去。这几年,一些很受欢迎的播客在主理人的新鲜感过了之后,就因各种原因相继停播。
从专业角度来看,方舟认为不少播客在制作上缺乏专业度,有时连最基本的声音质量、剪辑逻辑与语言表达都存在很多问题。随着今年各种资本、互联网平台的入局,他相信,商业化的过程也会是规范化的过程,播客的火热,会吸引越来越多专业人士进入,逐渐提升起播客的技术标准。
现在的播客,从某种程度上,就像2012年微信公众号刚诞生时那样,大家都能做,但还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最好的。这个逐渐摸索、完善的过程,也是令人期待的。
刘飞认为,播客不太可能变成大众市场,但这个垂直领域足以养活一个中等规模产业链,也能让几十个头部播客团队破圈。他很期待“小宇宙”能成为播客的头部平台。
跟视频相比,播客无论是质量、体量还是用户渗透率都相差甚远。尽管很多人把2021年称为“播客元年”,但它还远未到“风口”的程度。播客先要靠时间建立起行业标准,做出足够的质量和数量,那之后,才能谈论播客产业链与播客商业化。